2022-10-24作者:噼哩噗噜来源:www.pilipulu.com次阅读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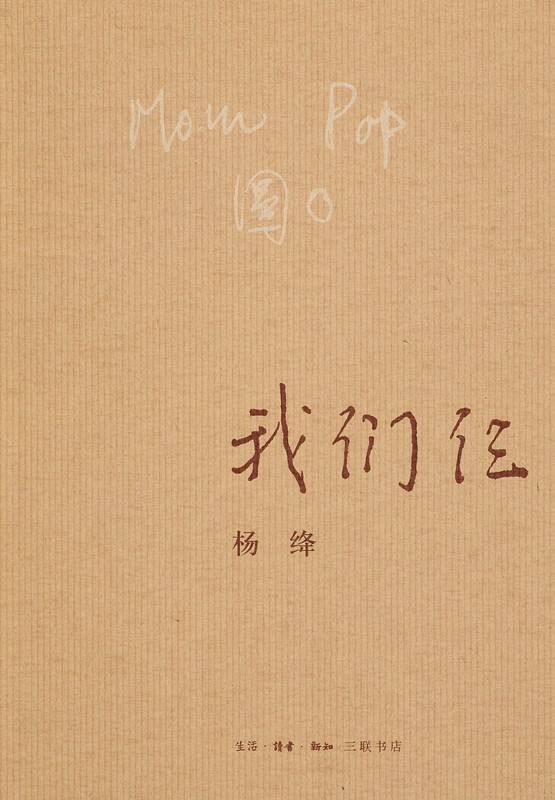
2018年11月,阅读。
前数日听余英时先生在国会图书馆演讲,内中如此评价钱钟书:
”He probably read all classics in all languages“.
钱钟书先生当然是所有文科生的偶像。她的女儿,”阿圆“也不遑多让,早年的”读书胚子“,日后“桃李满天下"。现在我每日钻研的英文文体学,竟也由她传来。
杨绛先生,则对我来说意义更重大,她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小说(1/2)堂吉诃德的最佳中文译者。当然,还有这本《我们仨》。
这样的文字,读来如沐春风。事过境迁,我身不能至,权摘抄其中牵动思绪之处,依时间与关系编排,心里向往一番,以下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钱钟书初到牛津:
“他初到牛津,就吻了牛津的地,磕掉大半个门牙。他是一人出门的,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,车就开了。他脸朝地摔一大跤。那时我们在老金家做房客。同寓除了我们夫妇,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,一姓林,一姓曾,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囗家。钟书摔了跤,自己又走回来,用大手绢捂着嘴。手绢上全是鲜血,抖开手绢,落下半枚断牙,满口鲜血。我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。幸同寓都是医生。他们教我陪钟书赶快找牙医,拔去断牙,然后再镶假牙。"
请看老钱在他的天堂:
”牛津的假期相当多。钟书把假期的全部时间投入读书。大学图书馆的经典以十八世纪为界,馆内所藏经典作品,限于十八世纪和十八世纪以前。十九、二十世纪的经典和通俗书籍,只可到市图书馆借阅。那里藏书丰富,借阅限两星期内归还。我们往往不到两星期就要跑一趟市图书馆。我们还有家里带出来的中国经典以及诗、词、诗话等书,也有朋友间借阅或寄赠的书,书店也容许站在书架前任意阅读,反正不愁无书。“
天堂也不尽然,信书不如无书:
”钟书通过了牛津的论文考囗试,如获重赦。他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,很不值当。他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,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。因此他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:“文学学士,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。”钟书从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。我们虽然继续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,我们只各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。巴黎大学的学生很自囗由。“
老钱当爸爸:
”我以为肚里怀个孩子,可不予理睬。但怀了孩子,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。在低等动物,新生命的长成就是母体的消灭。我没有消灭,只是打了一个七折,什么都减退了。钟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我:“晚,季总计今年所读书,歉然未足……”,笑我“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,又欲作女博士……”
钟书很郑囗重其事,很早就陪我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囗家大夫。院长问:“要女的?”(她自己就是专囗家。普通病房的产妇全由她接生。)
钟书说:“要最好的。”"
钱钟书回国后,还能如此戏谑领袖:
“钟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,早车去,晚上老晚回家。一次他老早就回来了,我喜出望外。他说:“今天晚宴,要和‘极峰’(蒋囗介囗石)握手,我趁早溜回来了。”
到1949,他无处可走:
”我们如要逃跑,不是无路可走。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,决定他何去何从的,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。我们从来不唱爱囗国调。非但不唱,还不爱听。但我们不愿逃跑,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,撇不开自家人。我囗国是国囗耻重重的弱国,跑出去仰人鼻息,做二等公囗民,我们不愿意。我们是文化人,爱祖国的文化,爱祖国的文学,爱祖国的语言。一句话,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囗姓,不愿做外国人。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,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囗海,等待解囗放。“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三反:
“三反”是旧知识分囗子第一次受到的改造运动,对我们是“触及灵魂的”。我们闭塞顽固,以为“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”,人不能改造。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,“发动起来的群众”,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,都随着按钮统囗一行动,都不是个人了。人都变了。就连“旧社囗会过来的知识分囗子”也有不同程度的变:有的是变不透,有的要变又变不过来,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偷偷儿不变。
我有一个明显的变,我从此不怕鬼了。不过我的变,一点不合规格。“
你们都洗干净了,也就是你们都和我们一样脏了:
“钟书就像阿瑗一样乖,他回校和我一起参加各式的会,认真学习。他洗了一个中盆澡,我洗了一个小盆澡,都一次通过。接下是“忠诚老实运动”,我代他一并交待了一切该交待的问题。我很忠诚老实,不管成不成问题,能记起的趁早都一一交待清楚。于是,有一天钟书、我和同校老师们排着队,由一位党囗的代表,和我们一一握手说:“党信任你。”我们都洗干净了。”
失去了选择,就失去了尊严:
“钟书很委屈。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,不是科班出身。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,教的是外国文学。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,也属外文组。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,他并不愿意。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,也赞许他的明智。钟书肯委屈,能忍耐,他就借调在古典文学组里,从此没能回外文组。”
那个阴冷的1957:
“接下来就是领囗导号召鸣放了。钟书曾到中囗南囗海亲耳听到毛主囗席的讲话,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,并未想到“引蛇出洞”。但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,听到各种论说,方知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事,使我们对“政治”悚然畏惧。”
我们真的没什么威胁:
钟书到清华工作一年后,调任毛选翻译委囗员会的工作,住在城里,周末回校,仍兼管研究生。毛选翻译委囗员会的领囗导是徐永焕同志,介绍钟书做这份工作的是清华同学乔冠华同志。事定之日,晚饭后,有一位旧友特雇黄包车从城里赶来祝贺。客去后,钟书惶恐地对我说:“他以为我要做‘南书房行走’了。这件事不是好做的,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。”
“无功无过”,他自以为做到了。饶是如此,也没有逃过背后扎来的一刀子。若不是“文化大革囗命”中,档囗案里的材料上了大字报,他还不知自己何罪。有关这件莫囗须囗有的公案,我在《丙午丁未纪事》及《干校六记》里都提到了。我们爱玩福尔摩斯。两人一起侦探,探出并证实诬陷者是某某人。钟书与囗世囗无囗争,还不免遭人忌恨,我很忧虑。钟书安慰我说:“不要愁,他也未必能随心。”钟书的话没错。这句话,为我增添了几分智慧。
其实,“忌”他很没有必要。钟书在工作中总很驯良地听从领囗导;同事间他能合作,不冒尖,不争先,肯帮忙,也很有用。他在徐永焕同志领囗导下工作多年,从信赖的部下成为要好的朋友。他在何其芳、余冠英同志领囗导下选注唐诗,共事的年轻同志都健在呢,他们准会同意我的话。钟书只求做好了本职工作,能偷工夫读他的书。他工作效率高,能偷下很多时间,这是他最珍惜的。我觉得媒孽都倒是无意中帮了他的大忙,免得他荣任什么体统差事,而让他默默“耕耘自己的园地”。
我们欠了人口民的债:
”三年困难”期间,钟书因为和洋人一同为英译毛选定稿,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。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。我们还经常吃馆子。我们生活很优裕。而阿瑗辈的“年轻人”呢,住处远比我们原先小;他们的工囗资和我们的工囗资差距很大。我们几百,他们只几十。“年轻人”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囗子。“旧社囗会过来的老先生”和“年轻人”生活悬殊,“老先生”未免令人侧目。我们自己尝过穷困的滋味,看到绝大多数“年轻人”生活穷困,而我们的生活这么优裕心上很不安,很抱歉,也很惭愧。每逢运动,“老先生”总成为“年轻人”批判的对象。这是理所当然,也是势所必然。
《宋诗选注》虽然受到批判,还是出版了。他的成绩并未抹杀。我的研究论文并无价值,不过大量的书,我名正言顺地读了。我沦陷上囗海当灶下婢的时候,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?我们在旧社囗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。因为时间就是生命。在新中国,知识分囗子的生活都由国囗家包了,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,只需全心全意为人囗民服囗务。我们全心全意为人囗民服囗务,只是我们不会为人囗民服囗务,因为我们不合格。然后国囗家又赔了钱重新囗教育我们。我们领了高工囗资受教育,分明是国囗家亏了。“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趣事一箩筐:
”我联想起三十多年后,一九七二年的早春,我们从干校回北囗京不久,北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。我晚上把煤炉熄了。早起,钟书照常端上早饭,还赺了他爱吃的猪油年糕,满面得色。我称赞他能赺年糕,他也不说什么,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儿。我吃着吃着,忽然诧异说:“谁给你点的火呀?”(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,他早上打开火门,炉子就旺了。)钟书等着我问呢,他得意说:“我会划火柴了!”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,为的是做早饭。
这年冬天,钟书和我差点儿给煤气熏死。我们没注意到烟囱管出口堵塞。我临睡服安眠药,睡中闻到煤气味,却怎么也醒不过来,正挣扎着要醒,忽听得钟书整个人摔倒在地的声音。这沉重的一声,帮我醒了过来。我迅速穿衣起来,三脚两步过去给倒地的钟书裹上厚棉衣,立即打开北窗。他也是睡中闻到煤气,急起开窗,但头晕倒下,脑门子磕在暖气片上,又跌下地。我把他扶上囗床,又开了南窗。然后给他戴上帽子,围上围巾,严严地包裹好,自己也像严冬在露天过夜那样穿戴着。我们挤坐一处等天亮。南北门窗洞囗开,屋子小,一会儿煤气就散尽了。钟书居然没有着凉感冒哮喘。亏得他沉重地摔那一跤,帮我醒了过来。不然的话,我们两个就双双中毒死了。他脑门上留下小小一道伤痕,几年后才消失。“
"死到临头还嘴硬":
"袁水拍同志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,可是我和钟书很顽固。他先说,屋子太小了,得换个房子。我和钟书异口同声,一个说“这里很舒服”;一个说“这里很方便”。我们说明借书如何方便,如何有人照顾等等,反正就是表示坚决不搬。袁辞去后,我和钟书咧着嘴做鬼脸说:“我们要江青给房子!”然后传来江青的话:“钟书同志可以住到钓囗鱼台去,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,照顾钟书同志。”我不客气地说:“我不会照顾人,我还要阿姨照顾呢。”过了一天,江青又传话:“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囗鱼台。”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,两人都呆着脸,一言不发。我不知道袁水拍是怎么回话的。"
"《管锥编》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,在这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,是“文化大革囗命”时期的产物。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,不用浅易的文言,而用艰深的文言。当时,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,正逞威横行。《管锥编》这类著作,他们容许吗?钟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囗由而已,他不用炫耀学问。"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感念其风骨,哀乎其不存:
“嘤其鸣兮,求其友声。”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,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。钟书是坐冷板凳的,他的学问也是冷门。他曾和我说:“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。”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已,不求有名有声。
我们读书,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。我们使用绳子,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。坐冷板凳的书呆囗子,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;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做绳子使用。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我们三个就是幸福快乐的一家:
”我们仨,却不止三人。每个人摇身一变,可变成好几个人。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,我三姐就说:“你们一家呀,圆圆头最大,钟书最小。”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。阿瑗长大了,会照顾我,像姐姐;会陪我,像妹妹;会管我,像妈妈。阿瑗常说:“我和爸爸最‘哥们’,我们是妈妈囗的两个顽童,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,只配做弟囗弟。”我又变为最大的。钟书是我们的老师。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,虽然近在咫尺,我们如有问题,问一声就能解决,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,我们都勤查字典,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。他可高大了。但是他穿衣吃饭,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,他又很弱小。“
“我们三个人就此分散了。‘世间好物不坚牢,彩云易散琉璃脆’。现在,只剩下我一人。”
“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‘我们家’的寓所,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。家在哪里,我不知道。我还在寻觅归途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活过,就是永远活过。祝你们幸福。
原文链接:https://book.douban.com/review/4658624/
作者:NeoCon
凡本站注明“本站”或“投稿”的所有文章,版权均属于本站或投稿人,未经本站授权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。本站已授权使用的作品,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,并注明“来源:某某站”并附上链接。违反上述声明者,本站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。